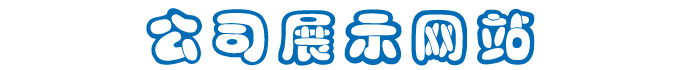
我出生在陜西關中平原,父母是地道的農民,可我從小喜歡畫畫,中學時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報考美術學院,讓我的夢想化為泡影。1968年初中畢業,我和千千萬萬個老三屆一樣,響應黨的號召,返鄉務農。那個年代雖說是一個荒廢的年代,卻也鍛煉人。在農村,我的畫畫特長有了用武之地,畫過毛像、、畫過土電影(幻燈片)。我忘不了在蒲城縣文化館業余美術組學畫的那段艱辛而又充實的日子,每個星期天騎自行車往返一百多里,參加縣文化館每周末舉辦的美術學習,現在看來,那算是我藝術人生中唯一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深造,盡管是短暫的。我忘不了那一時期給予我關心和幫助的中學老師韋宏達、蒲城縣文化館的美術老師高起勝。 1972年初西安美術學院開始恢復招生,這是我期待多年的夢想,在眾多考生中我的成績名列前茅,可萬萬沒想到,因為填表時我在婚姻狀況一欄里老老實實寫上了已婚,結果政審時被取消了。從此,美院夢跟我擦肩而過,我為之痛哭一場。時隔半年,秦腔劇團來陜招生,其中要招一名舞臺美術人員,這對我來說又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那時,對我一無所知,只聽說很遠很遠,可我不在乎,只要能有份畫畫的工作就行。我幸運地被錄取了,當時別提有多高興。可怎么也沒想到這一步跨出,我就再也無法離開。就這樣,我舍下了年邁的父母和新婚的妻子來到了。 我在上中學時就把父母給我取的名字春生改成了“鷹”,這正是之中我和的一份情緣,不正是鷹的故鄉嗎?命運把我帶到了,我本該屬于! 剛進藏時,我住在拉薩八廓街東南角一座古老的藏式庭院里,這里是秦腔劇團所在地。后來才知道這座庭院原來是舊藏官員索康家的宅院,是當時八廓街里典型的藏式庭院之一,庭院的西面三層閣樓朝東,其余三面兩層廊房環繞,中間是一個大的院子,院子中間有一口水井,除了我們這些住在院里的人,附近居民都從這口井里背水,大家的關系處得非常好,像一家人。我對的了解就是從這里開始的。每天進出八廓街,耳濡目染著濃濃的藏域風情,至今都懷念那段難忘的經歷,盡管那時生活條件很差。后來我之所以的民俗風情,應該與最初在八廓街里的熏陶和感染分不開。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八廓街里很差,相比今天的八廓街可真是天壤之別。但那時的八廓街很淳然、很真實。走進八廓街里有種撲面而來的藏風、藏味。也許是我在八廓街里住久了的原因,對那里有了濃厚的感情,甚至當時八廓街里讓人難以接受的氣味在我認為也是拉薩特有的一種生活氣息。雖然這輩子我跟大學無緣,可我從沒后,我和的這份情緣是無法用任何一所大學來衡量和比擬的。就是我的大學。剛進藏那些年里,我幾乎天天處于高度亢奮的狀態,每天背著畫夾或油畫箱,不知疲倦地穿行在拉薩的大街小巷、城郊田園,甚至搭乘便車到數百公里以外的鄉村、草原去寫生,留下了數百幅油畫、素描和速寫作品。因為太喜歡畫畫,我很快把自己融入到人的生活與文化中。 1983年,組織上調我到藏劇團工作,這又是我藝術人生的一次大轉折,也是我被帶入藏文化領域的一個契機。從此我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文化領域,藏戲中蘊含的特色文化和藝術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也徹底改變了我。我的審美觀開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藏戲中我看到傳統文化的特性和人類根性文化的特征,我也從中找到了現代藝術與原始文化的契合點。1988年,我設計傳統藏戲《白瑪文巴》的舞臺布景,正是利用古老藏戲中原始的表演形式與現代思維相結合,后來這個舞臺設計應邀參加了1989年的“上海國際舞美藝術節”,用一個專家的話說,在當時國內這是一個設計超前的舞美藝術創作。正是因為對藏戲的理解轉而對傳統文化的酷愛,我開始明白,發現美和創造美一樣重要,的美無處不在,我開始迷上攝影,用鏡頭記錄無處不在的美和那些美的創造者們。1986年,我擔任《中國戲曲志·戲卷》、《音樂集成》圖片編輯,更有機會到各地采風拍攝,相機替代了手中的畫筆,從此埋頭于民俗攝影。我永遠忘不了和好友邊多先生一起下鄉的日子,我在藏文化方面的知識都是得自于他的傳授,邊多不僅是我多年的摯友也是我最的老師。就這樣,不經意間我又成了名副其實的民俗攝影家。以至今天沒多少人知道我會畫畫。其實,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攝影就是我畫畫之余的最愛,那時我拍照片目的是收集畫畫的素材,沒曾想幾十年后這些照片成了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 自2000年以來,我大多時間用在編書,先后出版了《藝術》叢書、《民間藝術》叢書、《人文》叢書等。說來也慚愧,我說是初中畢業,不過是高小文化水平,記得剛到時我寫給中學老師的信,老師修改后又寄給我。所以過去除了想畫好畫我從沒敢想過寫文章編書,可沒想到后來還真的出了一大堆書,用朋友的話說我這是積淀深厚,到時候自然溢出來了。我心里很清楚,這是文化的力把我推上了浪尖,是時代的需要,歷史的需要。我在的大文化中一步步長大,又一步步成熟。 因為熱愛畫畫我來到,后來因為愛上就愛上了文化,也就愛上了攝影;這就有了數以萬計的圖片積累。如果《人文》叢書的出版對我來說是一種成功,也可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而每一次編書的過程都是我對藏文化認識上的一次。也許正是這些豐厚的積累和對藏文化深層的理解,我的畫開始變了,變得熱烈,變得深沉,變得厚重。我熱愛自然、熱愛生活,更熱間文化。這樣說來我多年的攝影、寫文章編書并不算是彎,而是我情感世界的鋪墊,最后這種情感將歸結到我的畫中去,因為對我來說感情只能通過畫筆來表達,畫畫才是我生命的靈魂。 轉眼我到就四十年了。我在這近四十年的經歷是多變的,也是充實的。我的性格決定了我的一生,干什么愛什么,鉆研什么(也許是自學的原因),朋友常常介紹我時不知道該怎么說,是畫家、攝影家、民俗學家,我笑答“雜家”。好友韓書力多次規勸“善取不如善舍”,我也曾下過決心,可對我來說舍去哪一塊都好像割去我的心頭肉,是文化情結一直在糾結著我的心。現在書也出了不少,我的心開始回歸到原初,回到畫的世界。其實這么多年來我并沒有完全放下過畫筆,《酒歌》、《古道》、《耕》、《山村》、《遠山》等三十多幅畫,都是在我編書的過程忙里偷閑畫的,多年來我習慣了雜亂的工作,反倒覺得很充實。一個人的成長不是孤立的,我在幾十年的進步與成長曾得到過很多人的幫助,都銘記在心。韓書力是我多年的摯友和老師,我們差不多同年進藏,又一起走到今天,用吳作人先生的話說,我們都是“嫁到”的人,他對藝術的與追求一直影響著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我的油畫寫生正處入時期,是陳丹青給我上了油畫色彩寶貴的一課,他曾極力舉薦我到中央美院,但都因為我當時工作不能,單位不放,永成遺憾。我還忘不了余友心老師以及不少畫界朋友的幫助。我更忘不了我的許許多多藏族朋友們,他們才是我永遠的老師。 2011年正好是和平解放六十周年,六十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我有幸親歷了以來迅速發展的三十多年。“四十年雪域情痕”正是四十年來我對不解的一份情緣。畫冊按年代分為四個部分,也是我在不同時期對的認識和理解,也寓意著的進步與發展歷程。為了增進作品的歷史感和文化內涵,我為每幅作品配了相應的短文。我想,就我的畫本身還顯得不夠成熟,但大多樸實,少一些張揚,這也許是我為人的風格。我只想通過這些畫告訴人們,這就是我心目中真實的。 說八廓街是的窗口一點不假,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一頭扎進這里,每天感受著八廓街的氣息,目睹八廓街里的瞬息變化。應該說,的變化最先從八廓街里人的變化開始。我剛到拉薩那幾年,拉薩流動人很少,每天轉經的多都是拉薩的老人,而且寥寥無幾。1976年,八廓街里的人開始多起來,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八廓街里已是人潮如涌,他們多都是來自藏北和康區的牧民,所以滿街看到的都是羊皮藏袍,有年邁的老人、有強健的康巴漢子、有純情的牧民少女……他們的身上散發著只有大自然才擁有的那種原始美,他們的眼睛里流露著一種人本真的純真與自然,還有那種充滿雕塑感的紫銅色肌膚,這種感覺就像一種高強的磁石在緊緊的吸引著我。 進藏開始那幾年我每天都泡在八廓街里,畫素描、速寫,油畫寫生。雖然我這一生沒能上過任一所美術院校,但我卻有幸在八廓街里泡了幾年,這是我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拉薩畫畫的人很少,有的是的美編,有的是劇團或展覽館等文化單位的美工,因著相同的愛好大家經常在一起互相,互相學習。我剛參加工作不久,對學習畫畫的渴望非常迫切。還記的我剛到拉薩時,美術界有影響的老同志就數歌舞團的褚友韜和日的馬剛等,他們自然成了我時常拜訪的老師。1973年,日報上發表了我剛進藏不久隨劇團支農收割時畫的一幅速寫《割青稞》,這是我第一次發表作品,當時的高興不亞于2010年我的油畫《酒歌》被中國美術館收藏。可以說,這兩幅作品是代表了我的繪畫生涯中兩個不同時期的開端。 從1972年到以后的那些年里,除了完成舞臺設計制作,其余的時間我全用在寫生上。應該說這十年是我風情畫創作的。濃濃的藏域風情在感染著我。當時的拉薩很淳樸。從美術的角度,周圍的人和景物呈現在一片灰色的基調中,恰是這種灰色給人一種幽靜而神秘的感覺。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朝佛大軍席卷拉薩,這座千年古城失卻了往昔的幽靜,但卻平添了一種渾厚的壯觀,那種壯觀來源于一種厚重,是把各種顏色揉在一起的那種厚重。黑、紅、黃、白、藍渾然一體,既不沉重,也不跳躍。就這樣,純然的灰色基調成了我那一時期的創作風格。 張鷹(1950.3—)陜西蒲城人。擅長油畫。自學美術,先后在秦劇團、豫劇團、藏劇團從事舞臺美術設計,1983年調民族藝術研究所從事美術編輯、民間藝術研究。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副研究員。作品有《高原之秋》、《鼓手》、《牦牛舞》、《風景寫生》等。出版《神舞、戲劇及面具藝術》、《面具》、《脫模泥塑》。編著《中國民間藝術全集·卷》。主編《民間藝術叢書》等。 版權聲明:凡注明“來源:中國網”或“中國網文”的所有作品,版權歸高原()文化有限公司。任何轉載、摘編、引用,須注明來源中國網和署著作者名,否則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在四川省自貢市自流井區仲權鎮竹元村,密林修竹中掩映著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院:小青瓦、樁板墻,透過歷史的煙塵,無聲地訴說著往事。[詳細] 當月25日,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軍途中,在江西省萍鄉市蘆溪縣上埠鎮境內的山口巖村遭到武裝伏擊,起義總指揮盧德銘在戰斗中英勇,年僅22歲。[詳細]
|